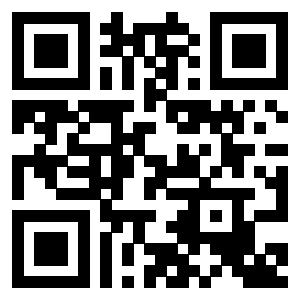苏雪林:我们的秋天:金鱼的劫运
S城里花圃甚多,足见花儿的需要颇广,不但大户人家的亭,要花点缀,便是蓬门筚窦的人家,也常用土盆培着一两种草花,虽然说不上什么紫姹红嫣,却也有点生意,可以润泽人们枯燥的心灵。上海的人,住在井底式的屋子里,连享受日光,都有限制的,自然不能说到花木的赏玩了,这也是我爱S城,胜过爱上海的原因。
花圃里兼售金鱼,价钱极公道:大者几角钱一对,小的只售铜元数枚。
去秋我们买了几对二寸长短的金鱼,养在一口缸里,有时便给它们面包屑吃,但到了冬季,鱼儿时常沉潜于水底,不大浮起来。我记得看过一种书,好像说鱼类可以饿几百天不死,冬天更是虫鱼蛰伏的时期,照例是断食的,所以也就不去管它们。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和暖,鱼儿在严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温和的太阳唤醒了潜伏着的生命,一个个圉圉洋洋,浮到水面,扬鳍摆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里,闪闪的金鳞,将水都映红了。有时我们无意将缸碰了一下,或者风飘一个榆子,坠于缸中,水便震动,漾开圆波纹,鱼们猛然受了惊,将尾迅速地抖几抖,一翻身钻入水底。可怜的小生物,这种事情,在它们定然算是遇见大地震,或一颗陨星!
康到北京去前,说暑假后打算搬回上海,我不忍这些鱼失主,便送给对河花圃里,那花圃的主人,表示感谢地收受了。
上海的事没有成功,康只得仍在S城教书,听说鱼儿都送掉了,他很惋惜,因为他很爱那些金鱼。
在街上看见一只玻璃碗,是化学上的用具,质料很粗,而且也有些缺口,因想这可以养金鱼,就买了回来,立刻到对河花圃里买了六尾小金鱼,养在里面。用玻璃碗养金鱼,果比缸有趣,摆在几上,从外面望过去,绿藻清波,与红鳞相掩映,异样鲜明,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鱼儿,像游在幻镜里,都放大了几倍。
康看见了,说你把我的鱼送走了,应当把这个赔我,动手就来抢。我说不必抢,放在这里,大家看玩,算做公有的岂不是好。他又道不然,他要拿去养在原来的那口大缸里,因为他在北京中央公园里看见斤许重的金鱼了,现在,他立志也要把这些金鱼养得那样大。
鱼儿被他强夺去了,我无如之何,只得恨恨地说道:“看你能不能将它们养得那样大!那是地气的关系,我在南边,就没有见过那样大的金鱼。”
——看着罢!我现在学到养金鱼的秘诀了,面包不是金鱼适当的食粮,我另有东西喂它们。
他找到一根竹竿,一方旧夏布,一些细铁丝,做了一个袋,匆匆忙忙地出去了,过了一刻,提了湿淋淋的袋回家,往金鱼缸里一搅,就看见无数红色小虫,成群地在水中抖动,正像黄昏空气中成团飞舞的蚊蚋。金鱼往来吞食这些虫,非常快乐,似人们之得享盛餐——呵!这就是金鱼适当的食粮!
康天天到河里捞虫喂鱼,鱼长得果然飞快,几乎一天改换一个样儿,不到两个星期,几尾寸余长的小鱼,都长了一倍,有从前的鱼大了。康说如照这样长下去,只消三个月,就可以养出斤重的金鱼了。
每晨,我如起床早,就到园里散步一回,呼吸新鲜的空气。有一天,我才走下石阶,看见金鱼缸上立着一只乌鸦,见了人就翩然飞去。树上另有几只鸦,哑哑乱噪,似乎在争夺什么东西,我也没有注意,在园里徘徊了几分钟,就进来了。
午后康捞了虫来喂鱼。
——呀!我的那些( )鱼呢?我听见他在园里惊叫。
——怎么?在缸里的鱼,会跑掉的吗?
——一匹都没有了!呵!缸边还有一匹——是那个顶美丽的金背银肚鱼。但是尾巴断了,僵了,谁干的这恶剧?他愤愤地问。
我忽然想到早晨树上打架的乌鸦,不禁大笑,笑得腰也弯了,气也壅了。我把今晨在场看见的小小谋杀案告诉了他,他自然承认乌鸦是这案的凶手,没有话说了。
——你还能养斤把重的金鱼?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