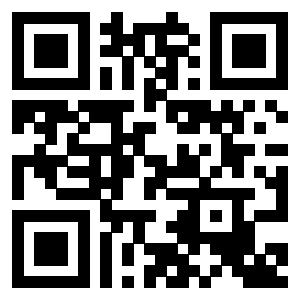父亲的份量
父亲的份量
文/空号
这些天,一直有个影子在眼前,间或而清晰地晃动着,让我心神不定,让我细泪盈眶,让我浮思掠忆。
那个影子就是我的父亲。他好像一直喃喃地试着给我述着什么,我那么认真地寻听着,却什么也没听到。我甚至有些惶恐了,我一直很硬强地生活着,莫非是什么坷坎要混沌了清洌的心绪,要不怎的会如此地脆弱,以至于惊扰了父亲的天国?
父亲已经逝去了五个足年了,真的不知道他在他天国怎么样了?我已经好些时间没有如此戚戚地念想着他,掂着父亲的份量了。
在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孱弱并且主动示退的人。在回忆中,父亲大多时候都是默不作声的,倚在人堆傍边地也看着热闹,生怕惊喜了人家一般,逢人都含着止着脚步的淡轻的微笑。人人都可以老远地或紧挨着扯开嗓门地呼着他的名字,换回他细脆的止着脚步的“啊、啊”的回应。正是父亲的这种的周遭和行事,一直让我们几个做子女的,脆弱着生活,坚硬地成长。
村里人大多时候都把父亲的孱弱归因于我的母亲,说是母亲的强势显衬了父亲懦弱。而母亲从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母亲的道理很简朴:男人的随性的躬让等于把执仗的戒尺交给了对方,而至于象父亲那样一个农村的男人没有生龙活虎的耕种技能也是不会被人顶得起来的。这两个弱项,父亲都占着份。所以只能是倔强的母亲默默地捡拾起了那些本该属于父亲的农活和街坊邻里的本领。久而久之,在我们村里,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便显出了倒置,父亲的份量也就有些偏失了。这一点,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感觉到了。
其实,父亲境况完全因为他是个木匠。一个典型的个体手工业者是不会去同时操练出一手农活把式的。只是因为出身成分好,为人卑谦,技艺超群,才至众口塑碑,好人一个,要不然大事小事还真没他说话的什么份。当然,要说到父亲的手艺,从先前手工业合作社到后来的十里八乡,不是登峰造极也可以说望其项背。业内的班班门门,他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就连我们几个兄弟,在一直的耳濡目染之中,做个门立条框也曾经是轻车熟路的了。
或许母亲是对的。父亲虽说生在农村,是个“农民”,却一年四季到队里上门户给人家打着木工活,从不上田插秧下地掘薯,基本上属于“四时”不辨“五谷”不分之人。所以一直以来,他的生活姿态都不够挺拨,总是有些“不务正业”的委身之感。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实行“包产到户”那年春耕,父亲“被迫”着下水田平地备秧。没料着大半天的时间,有着一身授绳直木本领的他硬是无法把那丘荡着泥水的田地平整好,生生地耽误着我们家几个手臂纤嫰手法稚拙的并不宽裕的春种时间,把倔强的母亲急成个哭笑不得。
好在父亲把手上技艺看得很重,练得很是精湛,因之而长久地收获着乡里乡亲难得的尊重。东家新屋刚做,都等着要他去封梁。西家嫁女,那十八般嫁妆都争着请他去做上个十天半月。那一家家图得都是他手下的鲜活的金刚钻和耐久的瓷器活,而父亲凭得都是他的成年累月品正质纯的齐缝对隼的精气神。他甚至可以只用一柄线锯和一把锉刀在一张普通的樟木床上上拉下剧左削右锉岀惟妙惟肖龙凤呈祥来,也可以随时起墨在人家刚竣工房屋的垛前檐后左描右绘上一排丰满生鲜的福禄寿禧案图。这些其实远非一个木匠的基本功课和应有技能了。
父亲也是个施之以教的好手,为艺数十年间,可谓是授有术教有方,桃李盈门。记得有一次,大概我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吧,父亲试着要和他一块拉大锯。因为站位和力度不得法,父亲似乎带着一丝狡诘的微笑应和着我,结果是无论我怎么用力,也始终无法拉动那片看着锋利尖滑的锯来。然后,他咕噜着比划地告诉我拉锯原理和诀窍:弓身斜用劲,轻推拉紧力,齿与墨线齐。如此一来一往你来我往,锯屑便纷纷洒下,材板也渐次清晰地展现开来了。如今思旧念新,我竟然还悟出点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来。或许当年父亲就是在交给我这些道理,只是他用的工匠的方法,技艺的态度。
父亲也很有些严厉的时候,大概他在外面憋屈的太多太久太主动的原因,我们一直如此地以为。比如,吃饭不准放声,端碗不可倚门。譬如,横着条纹的桌子不允许竖放,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可以乱层。林林总总分门别类乱心杂绪的,给了我们不少的岀错、挨骂捱揍的由头。每每那样,总有母亲的声音,哪那么规矩,谁让你们不长记性!争吵激烈的时候,父亲会经常丢失威严地训斥我们和母亲,并顺手把一些易拿好摔的家当弄得个劈劈啪啪,响声雷动。邻里往往会及时地出现,或指指点点或护三掩四,家里片刻间演义成了一出文争武斗的大戏来。
我一直理不清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我对父亲的领悟程度明显地胜于对我的母亲,也胜于我的兄弟姊妹,即便我十分清楚母亲之对我对家庭的作用更大了许多。这在我离开他们上大学进城工作成家立业自已也做了父亲之后,一直如此。我相信我的母亲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细微的差别。我没有那种父爱是天母爱是地的区分的意思,也不会因为父亲的“孱弱”而刻意偏执一方的做派,什么都说不清理不明。孝本来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禀赋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是不分彼此的。
我至今还常常叨叨着两件我和父亲的两件往事。都该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事情的发生都自然而然地与父亲的“弱势”有渊源上的关联。那个年代里,手工业者在我们那的生产队上是算不上一等劳力(壮年男丁)的,每天岀工挣的工分只与妇女差不了多少。如果是在队里或帮人做工是该上交工钱折算岀工分的。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小孩多,年底一摊分享的收成就少,要糊弄我们几个嫩牙稚口就真愁坏了母亲。好在还有一小块自留地,秋末总能收上个三五担地瓜。实在没法子,母亲大多时间都只能给我们煮红薯稀饭吃,最艰难的时候还会在稠饭里添些米糠和厥芽屑子来对付我们空乏着的胃。父亲那个时候也会默默地想着办法,补以口粮。有一次还没到过年的时候,父亲竟然裹着一包面条回来了,黑黑的土面条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足有三五斤重。他支开“小器”的母亲的劝阻,狠狠地下了一锅。那一次,我踏踏实实地享受了一次从来没有过的过饱的感觉,被撑的感觉,一个晚上嘟啷着个肚子无法入睡。
人常说饿如豺狼茹毛饮血。意思是人饿之极会饥不择食,见啥吃啥。小时候的我之于肥肉可着实是个例外,嗅嗅可以,吻都不会,除非炼成猪油兑着干饭。父亲或许生死瞧准了我这个死肋,一直变着戏法威逼利诱我那张幼小的嘴巴,都功败垂成。那一个春节,他满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先用五分钱最后到五毛钱换我吃一块他挑的全肥的肉,都让我的胆怯给败退回去了。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原由让我改变了这个戒忌,但每每这个时间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无论是他在生的时候还是故去之后。
父亲是个典型的“烟酒”生,对烟和洒有着天然的令人敬畏的嗜好。我分析这大概起因于乡亲们对他的手艺的尊重,而对他来说则正中下怀,因而前抱后揽左杯右樽吞云吐雾乐此不疲。每每在乡里乡亲家做事,无论餐前饭后休息片刻,业主总会献上仔细切好的烟丝或后来想方设法积攒下来的纸烟(香烟),以换取父亲的节奏加快废料减少和工艺更加精彩。至于酒,无论是白烧还是米酒,都是问客宰鸡看饭下菜,包括早上的热身,中午的减乏,和晚上收工,都得来上三五盅。这既是对木匠手艺的顶礼,也是对父亲名望的膜拜。后来参加工作有了收入之后,每次回家或有家人过往,我都会给父亲捎一些,我分明看到了父亲接到之后吸咂之时的那副阳光着的灿烂笑容。( )二OO二年我戒烟之后,曾经尝试着认真地和也谈过一次戒烟的事,被他用“一块肥肉”典故把我给滑稽了回去。可谁曾料到?五年后的一次孤独的夜行却绝然地扼去了父亲对烟和酒的敬仰。
那一次,爱着热闹的父亲提着手电晃荡如日出日落般地去邻家拉拾家常,却不然给跌上了一跤。到乡医所之后医生给了一个高血压的结论和戒烟戒酒按时服药的通知。没想父亲很凛然地接受了,从告别了他的烟酒人生。而待我再回老家见到他的时候,父亲的腋下已然多了一副拐杖,那年他才八十岁。
母亲在世时候曾经多次流露出过对那次变故的懊悔。每次回家她都会给我列数岀父亲的那些细微的变化,噙着眼泪地告诉过我,从那时候起,父亲会常常地默默地端着装裱有我和我的家人照片的他亲雕做的本质相框念念有词喃喃自语横研竖摩情不自禁。而我则越来越深刻感受到了父亲的无奈,我己然快看不着了他轻快的憨厚和生龙活虎了,我加快了回家的节凑。
但是,每次回到家里见着父亲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他那么的轻轻的轻轻地越来越迷糊地盯着我看的眼神,却分明是怕惊扰了我回家的心情。他每次都那么努力地放松着却又一直不自觉地细绷起来的他那张憨憨的轻脆地含着额头的笑脸。我知道,他在一直努力地感受着儿子的突然的出现,和随后隆烈的离开。他一定是在说,回家是儿子的期盼,远行才是父亲的寄托!
这些天,总有个影子在我的脑海里晃现,清晰而间或地晃动着。那个影子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喃喃地给我说着些什么,我始终在认真地寻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