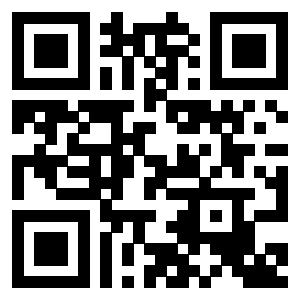韩春旭:一个固执的呼喊者
韩春旭:一个固执的呼喊者
徐春萍:这不是一部“浅阅读”的书,虽然它是一本散文集,但里面所收的文章与风花雪月无关,而是或多或少都带有哲学思辨色彩,可以说有些篇什读后令人陷入痛苦的思索。有一阶段,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大多强调私人话语,风格晦涩、琐碎。而你的《我的精神》,关心的对象可以说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话题。在今天这样一个谈时尚、谈小资、以各种各样的物质成就为荣的时代,这本书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因为它要谈精神、谈精神的成长、困惑、对话,谈人类的命运,谈生命,谈德行,谈爱心。你觉得今天讨论这些话题,有什么现实意义?
韩春旭:的确,当我将这本散文集起名《我的精神》时,自己也笑了,我在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与我有缘的人,拿起这本书,多少也会认为此人在玩深刻。”
其实,我丝毫没有一点意炫耀自己多么的高尚和不平凡。应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条向上延伸的精神曲线: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问题绝不仅仅只有哲学家才能发问。或者你已吃饱穿暖有着舒适的住房、奢华的汽车,或者你还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睡觉的窝,但这生命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曲线,总会伴着肉体的滋养而诞生。印度五千年前最古老的经典《博伽梵歌》中讲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人心中有意识要询问这类问题时,他才算是人。”
应该说我们的现实生活都依附在这条曲线上,并不知不觉地使它强大,只是人与人的点不同,人与人延伸到哪里的不同。
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十岁的孩子,在游戏厅里玩着通宵的游戏,不吃不喝,而后趴在那里孤单睡去的报道,我的眼泪禁不住湿了。现在的孩子们,从小泡在电视、电脑里;从小在歌星、影星的欢呼雀跃里,而后就是沉重的书包、沉重的分数、沉重的学位,孩子们似乎对“精神”二字,感到特别的遥远,或者就是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宣言。而我们现代生活的大人们,或是为了孩子,让他们在国内有更好的学校上,而后到国外又有更好的学校上,而后再有更好的工作去做,或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房子住,更好的汽车开,有更好的情人、爱人,都在拼命地奔波着。
如果说人类曾经有过崇尚理性、敬畏精神的世纪,眼下人们似乎很难再去相信肉眼看不见的虚幻的精神,甚至拒绝认为精神的存在。其实,“精神”恰恰是人性最本质的所在,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也就是“灵”在这里。
敬重看起来是满足肉体的,比如:吃、穿、性爱,这是正常的需要。但上帝赐给你这肉体,赐给你这些欲望,是让你在这种欲望中学会选择更高的存在状态,更高的存在经验。
你在吃、穿、性爱,成功、权利的享受中,是否更加经验和选择了善良、同情、慈悲、了解、平衡、宽容和爱,而不是贪婪、自私、憎恨、愤怒、奢速。
在今天,当人们能够在吃喝、性爱之时,渐渐地学会感受、寻觅、成长着精神,穿衣吃饭、娶妻生子、世俗世外自会有大乐,而这种乐是生命深处真正的需要。你最终会收获到“至小无内”、“至大无外”,通向无限光明、安宁、喜乐、爱和感恩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自己之中,似乎与天地流行的一种生命永恒的存在中。
我想说,这是人性深处真正的、本质的,也是永恒的需要,是伴随人类永远的话题。
徐春萍:许多学者谈哲学、谈思想、谈精神,常常囿于知识界学术界,而你的思索是可以与许许多多普通人共享的。你的文章有布道、启蒙的意味,但你不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这本书的语言很有激情和气势,颇有感染力。从一个作家的角度,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民族的文化建设、精神生活主要少了什么?
韩春旭:不论在创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的确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尤其我的笑声,许许多多的人都说“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感染力。尽管我已经四十多岁,许多朋友都说我是“阳光女孩”。
在散文《我的灵魂生活》中,我这样写道:我感觉我的生命是那样的辉煌而富丽,我感觉自己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奔放的爱的能量。我可以向天空、向大地、向周围的一切张开双臂,而后一种无穷无尽的欢乐就能与我对流。从寂静的树木草丛中,从袒露的石头泥土中,从悠悠的空气和风中,互相涌动,互相喷涌。
我这种面对自己而荡漾着的生命的醉意,的确是因为我精神上有着一种长年的坚守,是无限的精神滋养着我的身,也滋养着我的心。
随着我精神不断地成长,我越加热爱我的祖国,热爱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说来,我多年都是在西方哲学思想的邀游中,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叙本华、尼采、萨特……等等大师的长期的对话,近几年才开始捧读老子、庄子,甚至《周易》,在阅读与思考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东方圣贤智慧的精神和博大。
我认为,西方人总是在奔跑中思考。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样,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思考、追寻、困惑、挣扎、拼搏,而代表东方的中国人总像一尊卧佛,卧在一座高山顶上的石头上静观着一切。周围一事一物,万难万事,千变万变,但他们早已通晓变化万象中的那个永恒存在的“不变”,静观在那里,玩索而有得。
我想说,是中国的圣贤,中国的古老的智慧,使我懂得人生最应该懂得的,也是最简单的人生道理:人其实也同植物、草木、动物一样,都是天地交合之物。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感恩,感恩天地之养育。天底下哪有什么真正的“自我”,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你一分钟也活不下去。就是有空气、有水、有阳光,没有山、没有树木,没有好人、坏人,聪明的、蠢笨的人,你仍是无法活下去。我懂得了一切存在都相互依赖共存共生。我懂得了一生要感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能我的理解还非常浮浅)尤此,我更加热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城市,方正中体现的是“中和”,中国古老智慧的精髓。我喜欢我们中国绘画、书法、音乐、陶瓷、园林艺术、捏泥人、剪纸许许多多的民间手工艺术,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存在都是殊途同归,释译着中国古老而最高的智慧,释译着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和平的真正境界。
而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国,对于我们民族自身来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清醒地知道“坚守”,“坚守”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命运是多么的重要。
物质文明不如人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超越物质文明时,内在的一种精神也丧失了。“洗澡水和婴儿一并倒掉。”
看着我们的城市,古老建筑,古老的胡同大片消失,看着我们许许多多的民间艺术已失去传人,我的心里总是焦灼地面对着自己讲着一句话;人类一样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类毁灭的那一天。
徐春萍:有评论家称,你的散文倡导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这种说法的主要涵义是什么?
韩春旭:我想,不少的评论家称我的散文为新人文主义散文,这种相法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人文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张扬人的价值和人性的解放,那么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我们的科技文明,还是物质文明有了多大的发展,人类共同面临的仍是一个话题,也就是在古希腊戴尔菲城神庙碑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人类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类为了追求更多的幸福而最终丧失了包括人自身的一切。
评论家秦晋先生对我的新人文散文的涵义概括为三点: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反对由《圣经》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人类中心说”,我认为把人置于“主宰万物”的地位,是人最大的魔幻,从而失去了人应该遵循的本份,失去了与万物平等相处,和谐共生的前提。我在散文中,多次写道: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能没有地球,入仅仅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的秩序只有融合到地球秩序中去,人才能生存下去。
第二,精神与肉体的和谐。我一直认为精神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中更深层的生命,是生命中最本质的能量。肉体仅仅是精神的载体。我在散文中写道:“人类的肉体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它饱含着精神;人类的精神所以区别于上帝,是因为它植根于肉体。”人类的今天,如果还无节制地贪求物质享受,理性精神不断丧失,灵与肉二者分离,人类同样会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第三,进步与代价的和谐。人类文明的建立和发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达到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在散文中写道:“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同样能够致一个民族于死地。但是代价不是无条件无限度无原则的。无知就可以无畏的话,比如灭除其他物种,耗竭地球资源为代价,还有比人捣毁自己生存条件更荒诞的事情吗?!
秦晋先生在评论中这样说道:韩春旭的全部鼓作都在呼唤一种“平衡”:地球生态的平衡,人类精神的平衡和社会历史的平衡,她是平衡理论的倡导者。平衡论这一古典哲学,被韩春旭演化为一种现代思维,现实思维,积极思维,乐观思维。
我想,这大致就是新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涵义。
呼唤,这是一个作家所仅能做到的,作家凸凹先生说:“韩春旭是一个最真诚最固执的呼喊者。”
徐春萍:有思辨色彩的( )女作家不多。从文学到哲学,能不能具体谈谈“你的精神生活”?
韩春旭:许多人都说我的作品区别于女作家,甚至还有人讲:我的哲理和思辨已超越许多的男作家。
从我的天性来讲,对于思想怀有的兴趣,远大于对于知识的兴趣。从文学到哲学,或者说从哲学到文学伴随了我20多年。这多年坚守的精神生活身单纯而平静的,除了干好我一直都很喜欢的编辑工作以外,多年就是读自己想读的书,思想自己想感受的人和事物,而后坚持长年的每日独自散步,而后有些闲钱就去国内或国外感受自然、历史、文化和宗教,而后闲暇再和一些不同类型的好友闲聊,搓麻,打打球,而后再去写一些自己的确感觉可写的文章。
还有不能缺少的,每天听音乐。
在我看来,人生除了吃饭、穿衣,“有了快感你就喊”之外,其实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人需要学会走出去,还要走回来;需要学会无中生有,还要有中还无;需要学会从简单到复杂,再回归更高点的简单;还要学会极高智慧的“中和”。
- 韩春旭作品_韩春旭散文精选
- 韩春旭:韩春旭散文集序
- 王逸竹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