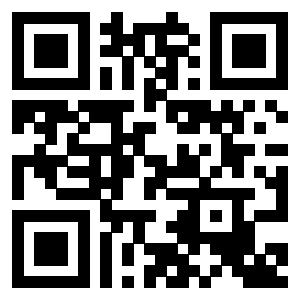泰戈尔:废纸篓
泰戈尔:废纸篓
“你在干什么,苏妮①?”父亲吃惊地问,“干吗把衣服装在皮箱里?你要去哪儿?”
苏娜丽达的卧室在三楼,有两扇南窗。窗户前床上铺着考究的拉克恼床单,对面靠墙的书桌上,摆着亡母的遗像,一串芳香的花条挂在墙上父亲照片的镜框的两端,粉红色地毯上杂乱地堆着纱丽、衬衣、紧身上衣、袜子、手帕……身边,摇着尾巴的小狗举起前爪往女主人怀里伸过去,它不明白女主人为什么收拾衣服,生怕女主人扔下它不管。
妹妹莎米达抱膝而坐,侧脸望着窗外,她没有梳头,眼圈红红的,显然刚才哭过。
苏娜丽达不答话,只管低头整理衣服,手微微发颤。
“你要出门?”父亲又问。
苏娜丽达口气生硬地说:“你讲过,我不能在家里成亲,我到阿努②家去。”
“啊呀!”莎米达叫起来,“姐姐,你胡说什么呀!”
父亲露出恼怒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他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他们的意见,我得一辈子听从。”女儿语气坚定,表情肃穆,决心不可动摇,说罢把一枚别针装入信封。
父亲忧心忡忡:“阿尼尔的父亲鼓吹种姓制度,会同意你俩的婚事?”
“您不了解阿尼尔,”女儿自豪地说,“他是个有主见、胸怀坦荡的青年。”
钟敲了十二下。
苏娜丽达一上午没有吃饭。莎米达来叫过一回,可她非要到朋友家吃不可。
失去母爱的苏娜丽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也要进屋劝女儿吃饭,莎米达拉住他说:“别去了,爸爸,她说不吃是决不会吃的。”
苏娜丽达把头伸到窗外,朝大街上张望。终于,阿尼尔家的汽车开来了。她急忙梳妆,一枚精巧的胸针插在胸前。
“拿去,阿尼尔家的信。”莎米达把一封信丢在姐姐怀里。
苏娜丽达读完信,面如死灰,颓然坐在大木箱上。
阿尼尔在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改变父亲的观点,岂料磨破嘴唇,他仍固执己见,所以……下午一点。
苏娜丽达呆坐着,眼里没有泪水。
仆人罗摩查里塔进屋低声说:“他家的汽车还在楼下呢。”
“叫他们滚!”苏娜丽达一声怒吼。
她养的狗默默地趴在她脚边。
父亲得知事情发生突变,没有细问,抚摸着女儿的柔软的头发说:“苏妮,走,到赫桑巴特你舅舅家散散心。”
明天举行阿尼尔的婚礼。
阿尼尔执拗地叫嚷:“不,我不结婚。”
“你疯啦!”父亲勃然大怒。
阿尼尔失魂落魄。
傍晚七点左右,苏娜丽达家的一楼里点着煤油灯,污渍斑斑的地毯上摞着一叠报纸。管家卡伊拉斯·萨尔加尔左手托着水烟筒抽烟,右手呱嗒呱嗒扇着蒲扇,他正等听差来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
阿尼尔突然来临。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乱之中忘了给( )喜钱,想起了特地来一趟。”阿尼尔犹豫一下说,“我想顺便再看一眼你家苏娜丽达小姐的卧室。”
阿尼尔慢步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床具上,门框上,窗帘上,漾散着人昏迷呻唤般的幽微的气味,是柔发的?残花的?抑或是空寂的卧室里珍藏的回忆的?不得而知。
阿尼尔抽了会儿烟,把烟蒂往窗外一掷,从书桌底下取出废纸篓,捧在胸前。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他看见满篓是撕碎的信纸。淡蓝的信纸上是他的笔迹。此外还有一张照片的碎片,四年前用红绸带系在硬纸板上的两朵花——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