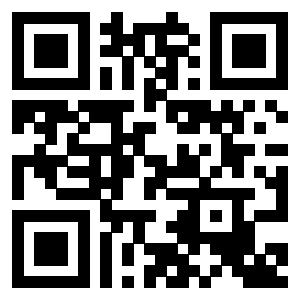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一个路遥就够了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最后“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迹显现,痛苦像灰霾一样散去,食物暂时疗愈了内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实是农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会干。姑娘率性地说: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待着。把他惊得哑口无言,慌不择路离开。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路遥将自己的婚恋观投射进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虽然心底深爱着刘巧珍,但为摆脱命运,仍选择了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
“想要突围”的心情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
曹谷溪大路遥八岁,延川县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时因支持“红总司”,被路遥派人抓进监狱。后两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调路遥到通讯组培训。在通讯组,路遥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林达性格单纯,文笔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秘书。与路遥恋爱后,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据说林虹大哭一场。
1973年夏天,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路遥再次因为“白振基”案,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在延川县文教局和县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证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与路遥无关。
1973年秋,路遥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个头不高,看着敦实厚道。入学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黄帆布背包,“匈奴须”被仔细刮掉,脸青亮青亮的,嘴角透着微笑。他凭出色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班长。
林达每月38块的工资,大部分支援了路遥,剩下的维持自己简朴的日常生活。在后来路遥病危时,许多人虽然对林达心有指摘,但从未有人怀疑她这一生为路遥做过的牺牲。
1977年路遥毕业,留在《陕西文艺》(后来的《延河》杂志)当编辑。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一年后,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这时候的陕西作家群,人人都憋着股子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
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那时的路遥很苦恼,“想要突围”。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打来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
小说《惊心》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头条刊发。之后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延河》诗人闻频回忆,一个礼拜天,路遥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紧紧拥抱了他。
抽好烟,是心理需求
1981年夏,路遥住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昼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内转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怀疑他神经错乱。
路遥喜欢把自己投入这种如同炼狱一般的情境,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把身体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满谷满仓,富饶丰盈,这是他的基本人生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路遥父亲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实也是公家人欺负他家在“门外”不站人。路遥辗转托好几层关系向清涧县委书记说情,路遥父亲才得以释放。
权力,在城乡现实里所显示出的无往而不利的实用属性,以及底层农民对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遥的精神里,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遥特地到陕北着名的道教圣地白云山道观中抽了一签,显示“鹤鸣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2年11月推出单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象。
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七八个电视台要改电视剧,传达室的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路遥常常刚接完电话回到家中,一只脚还没落定,又要转身接下一个电话。年轻人把他奉为“人生导师”,一些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5年3月,36岁的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一起,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但是,路遥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象。他穷得叮当响,凑不齐去北京领奖的路费。
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一百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扞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遥已经功成名就时,他决心再次把自己投进“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写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
经过两年的前期资料储备,1985年秋,路遥带两大箱书籍和资料,十几条香烟,两罐雀巢咖啡,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写稿。在弟弟的张罗下,矿医院为他安排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
矿上生活艰苦,没有蔬菜,鸡蛋,豆腐都难买到。路遥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遥怀抱着二十多万字的手稿,赶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儿路远。他与妻子林达的夫妻关系已是强弩之末。两人无论家庭背景,还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差得太远。
许是小时候遭受的饥饿之苦仍在心头作祟,他在物质上对女儿绝不克扣,女儿要啥,他就买啥。
他曾借钱女儿买了一架很贵的钢琴,但最后也没用上,只得搁在家里的角落。女儿春游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后在凯悦酒店花60元买了两块。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它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看见的同事问。
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编辑周昌义。周昌义后来回忆,他在西安期间,常有人问:看路遥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许多人都不看好路遥的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周昌义也不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
路遥悲愤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身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伟的呼噜。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但路遥并不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给王震、陈永贵看过病的老中医张鹏举。
经过张鹏举的调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后,1987年10月下旬,路遥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则说:“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弟弟王天乐在路遥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路遥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苦难、殉道、“牛马般的劳动”,这是路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
路遥也改变了弟弟王天乐的命运。他写作成名之后,将勤奋、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又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
“田晓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地点在榆林宾馆,条件比之前强很多,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有一天,正在洛川县采访的王天乐突然接到《延安日报》社转来的电话,让他速去榆林。洛川离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赶到。等王天乐心急火燎赶到,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去世了。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气,劈头盖脸数落了路遥一顿。
又一次王在黄河壶口采访,路遥的电话又追来。原来是他的咖啡和烟用完了。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王天乐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领导。领导很热情,先拿来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并叮嘱每月送一次,经费由榆林财政出。
两个月后,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叶咏梅是在一年前坐电车时偶遇路遥,才拿到了这本书。叶咏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据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遥决定到他的风水宝地,《人生》的写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后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搏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
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像干渴的夸父
虽然《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1991年初,作家白烨提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他马上去给路遥打电报:“大作获奖,已成定局”。
当天下午,路遥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烨发来的喜报。
他兴奋得要跳起来,第一时间找到王天乐,告诉他获奖了,排名第一。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早在路遥写完第二部,身体面临崩盘之时,妻子林达就已提出离婚。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矛盾文学奖的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
身无分文的路遥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拿奖之后回到西安,贾平凹来向他庆祝。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路遥是拟定的主席人选。
他跟朋友们敞阔地聊天,到兴头上,信誓旦旦: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五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报名费就能挣不少。
朋友们问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说:你小看我,这次,我不仅要在国内获奖,还要拿国际大奖。
也有不可对人言的难堪处。他与妻子林达已达成离婚协议,林达放弃一切回北京联系工作调动。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对门的朋友家住。这一段时间,人们常看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陕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拟任他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但结果还没有最后公布。
但消息传开,省委很快派人来,安排他住进省城的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厚夫曾去医院探望,见他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像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达已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上班。
虽然有医院的全力抢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路遥去世,享年43岁。林达于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的后事。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