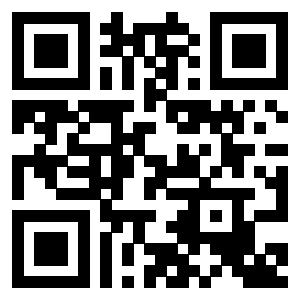没有低到尘埃里的种子不开花
没有低到尘埃里的种子不开花
文/七堇年
2010年我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出了新书,之后被拉去全国签售一圈。那种累不是体力的累,是心累,感觉像被人牵着当戏看。心像一个想飞的热气球,吊篮里却挂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飞不起来,觉得胀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却还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着。天天手脚冰凉,冷得发抖——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都只穿单裤出门的人。那会儿生活空荡荡的,喊一声都有回音。大雪天一个人骑车去游泳,泳池浮着薄冰,咬着牙扎进冰水里去,那滋味儿,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东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个。我一时间找不到事做,抑郁症复发,重得没法跟别人说。每天专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没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没缺胳膊少腿又没饿着冻着,抑郁什么?比比非洲难民,好意思吗?
老妈看出来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迹鼓励我,说:“你看人家崔老师抑郁了,就休息,出来做《我的抗战》,一个人走走长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吗?”我苦着脸说:“他是谁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老妈说:“你这么想就不对了啊!别人还会说,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闲得发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想过做杂志,但做杂志的人太多了,全都雷同,再做也没有意义;写东西吧,那会儿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青黄不接吧——年少时什么都敢写的劲儿过去了,该成熟的又没熟透,所谓瓶颈期吧,什么都写不出来。
做什么好呢,就这么漂着吗?漂泊之所以让人羡慕,那是因为你只见到了漂上去的,没见过沉下去的:后者才是大多数。什么事儿都是听上去很美,到了实处,要拿胆子来说话——心里掂了掂分量,这胆子我还真没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开始梦寐以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别人听说我要找工作,都问我:“你还找工作?你不好好写东西,找什么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了。
天天在网上刷啊刷,终于看到一个招聘消息,我立马把简历递过去。体制内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没爹,娘也没得拼,但还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着弯儿地联系上那个书记。后来听说,我妈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去年给硬塞进那个单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花了二三十万吧。
死马当活马医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又悲壮又凄凉。我和我妈就拿着简历,花血本买了两瓶酒,再商量半天,有点心疼地塞了一个红包在里面,跑了400公里长途,去拦那个书记。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书记家楼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来了。我远远看着母亲巴结着脸过去,递上我的简历和酒,书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不理会,没说两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来就阴冷,我心酸得泪都快掉下来。
当天我们往老家赶,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妈一路对我说风凉话,把我写东西得来的那点可怜的自信给踩得一塌糊涂:“出了你们那个圈儿,你就什么都不是——说白了,就算在那个圈儿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别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装腔作势、矫揉造作……”有时候,亲人的狠话最伤人,我一路上泪流满面,小小年纪心如死灰的感觉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点,我累极了,一脸泪痕,脸面紧绷发痛。我什么都没说,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时候,掀开被子,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在一束灯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尘。黑暗中,灰尘什么的没人看得见;灯光下,你才看得到,原来有这么多灰尘。
那个瞬间我突然想,如果说写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盏灯,照亮了你原本看不见的灰尘。它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飞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你可能不会知道有怎么样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
后来,那份工作的事儿,反正也找不到“后门”,就从“前门”走吧:硬着头皮面试,问什么答什么,讲了半小时。鬼使神差地,他们说我英文很好,录用了。
就这样,我也打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郁症渐渐好了。又开始觉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如果当初就着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现在很清闲?春花秋月,在杏花下喝酒?周游世界?哪像现在这样,忙得四脚朝天。
原来不光是选老婆,生活也是红玫瑰白玫瑰:梦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从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没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台榨汁机。没时间写作,没时间思考,生活不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堵在上下班高峰的路上,呼吸着汽车的尾气,连梦都累得没法儿做了。要人人都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GDP谁来贡献?
没低到尘埃里的种子,是开不出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