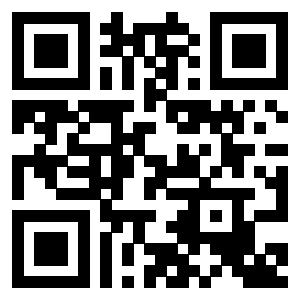人生的三类幸福
亚里士多德将人生的幸福分为三类:来自外面的幸福;来自灵魂的幸福;以及来自肉体的幸福。除了我们可以采用这种三分法外,这种分类别无所长。我认为,人的命运的差别可以归结到这样三种不同的原因上:
第一,人是什么,从广义上说,这就是指人格,它包括健康、力量、美、气质、道德品格、理智以及教养。
第二,人有什么,即财产与各种所有物。
第三,一个人在他人的评价中处于什么地位。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通过被了解到了的东西,一个人在朋友们眼中的形象如何,或者更严格地说,他们看待他的目光如何,是通过他们对他的评价表现出来,而他们的评价又通过人们对他的敬意和声望体现出来。
人们在第一方面的差别是自然造成的,仅从这一事实就可以断言,和另外两个方面的差别比较起来,这一方面的差别对于幸福与否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后者不过是人为的结果而已。与真正的人格优势,如伟大的心灵或高尚的情怀比较,那么,显赫的地位,高贵的身世,乃至王侯将相,充其量不过如同舞台上的王侯而已,而前者才是人生的真正君王。
很久以前,伊壁鸠鲁最早的信徒麦特罗多洛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著作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外在的幸福远不如内心的福祉。无可置疑,人生幸福最基本的要素——就整个人生来说——就在于人的构成,人的内在素质。这是由人的一切情感、欲望以及各种思想所引起的内心满足的直接源泉,而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则是间接的。
所以,同样的外部事件对不同的人其影响也就不同,甚至在许多外在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独有的小天地里。人最直接理解的是自己的观念。感觉以及意志,外部世界只能够在与生活有关的那些方面对人们产生影响,人们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方式于其中的世界来塑造生活的。
所以,对不同的人它就表现出不同的色调,对于一些人来说,它贫脊荒漠、枯燥乏味、浅薄空疏;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丰厚富实,趣味横生,意味深长。很多人听到别人经历了一些令人快慰的事情后,也期待着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生同样的事情,而忽视了他们更应妒嫉的是那种精神能力。
当人们描绘一些令人愉快的事件时,这种能力便会赋予这些事件以独特的意义,对于天才来说,它们充满了悦意的冒险情趣,而凡夫俗子由于感觉迟钝,这些事件在他们眼中则变得陈腐乏味,司空见惯。
歌德和拜伦的许多诗作就完全是天才的杰作,而这些作品显然也是根据现实写下的。愚蠢的读者因为诗人经历了那么多愉快的事情而妒忌他,但不去妒忌诗人无比的想像力,正是这种想像力把至为平凡的经验变得伟大辉煌。
同样,在自信乐观者看来只是令人兴奋的冲突性事件,在性格抑郁者看来则是一幕悲剧,而对于心灵麻木不仁的人来说,则没有任何意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个事实,即,要认识并欣赏任何事物,都要求有两方面因素的协作,即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这两者如水中的氧和氢一样必然地密切联结在一起,所以,尽管在经验中客观的或外在的因素相同,但由于主观的因素或个人的鉴赏力不一样,同一对象在不同人的眼中就会显出天壤之别,就仿佛这种客观因素也不一样了。
在智力迟钝愚蠢的人看来,世上最灿烂多彩的事情也是乏味无聊的,所以对它的欣赏也就乏味无聊,这就像一幅在晦暗天气里的优美风景画,或一架劣质摄像机暗门上的映像。的确,任何人都被幽禁在他自己意识的范围之内,人不能超越自己,更不能直接走出上述界限之外。
所以,外部的帮助对他并无多大意义。在舞台上,有人扮演王子,有人扮演大臣,有人扮演仆役,有人扮演士兵或将军,等等。这一切都只是外表的不同,脱下这些装束,骨子里大家都不过是一些对命运充满了忧虑的可怜演员而已。人生就是这样。地位和财富的悬殊使每个人扮演着适合自己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在的幸福和快乐有所不同,那些凡夫俗子,那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和烦恼也是根源于此。纵然幸福与不幸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但就这两者的根本性而言,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是极其相似的。
毫无疑问,幸福与人们必须扮演的角色、地位的浮沉以及财富的得失毫无关联。对人来说,一切存在或发生的事情都只存在于自己的知觉之中,只是相对知觉而发生。所以人最为本质的东西就在于这种意识的形成。一般而论,知觉要比构成知觉内容的环境重要得多,一个人要是麻木不仁,冥顽不灵,那么,只要他想一想塞万提斯被囚禁在冥室棱棺的悲惨情景下写作《唐·吉河德》,世上的一切荣耀和欢乐都会化为乌有。人生客观的部分掌握在命运之神手中,它会因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主观的部分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在本质上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尽管人们的外部条件可能发生很大变化,但每个人的生活都表现出存在着一致的地方,这就像同一主旋律上的一系列变奏。人不能超越自己。一个动物被安置在某一环境里,它就得局限在自然给它安排的这个狭小圈子里;人也是这样,人们孜孜以求幸福的努力永远都保持在其本性所许可的范围,被局限在能感觉到的程度;人所能获取的幸福的多少,预先就由他的人格所决定了。相对于我们精神的力量就更是如此。
这种精神力量与人们获得更高级愉悦的能力密切相关。如果这些能力弱小,那就会一事无成,亲朋好友以及命运能够给予他的,就不足以使他达到人们一般幸福和快乐的水准。他的一切都来自于肉体的欲望(一种极度舒适和令人惬意的家庭生活),粗野下流的同伴和粗鄙无聊的娱乐。
另一方面,一旦情况是这样,要开阔他的视野,即使教育也无济于事。人最为高尚最丰富多彩的永恒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青年时代则可能欺骗我们。心灵的快乐主要取决于心灵的力量。显然,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的人格。而命运或命运所先定加给我们的东西一般地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什么”,或我们的名誉。在这种意义上,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如果我们的精神上不够富有,那么我们的命运就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愚者依旧愚蠢,冥顽不灵者仍然冥顽不灵,甚至即使他们身边簇拥着众多的美女也是如此。
歌德在《西东胡床集》中写道,“对每个时代来说,无论是地位卑下的民众或奴仆,还是生活中公认的胜利者,他们作为尘世间的凡人,其最高的幸福仅仅是人格。”
有句谚语说,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从青年和老年不能共同生活这个事实,一直到天才和圣人的生活,所有的事实都说明,对于幸福来说,人生中的主观因素要比客观因素重要得多。健康比其他幸福重要得多,所以有人说,宁做健康的乞丐,不做多病的国王。温文尔雅、活泼快乐的气质,完美强壮的体格,健全的理智,敏锐的洞察力,稳健而温和的意志以及良知,这些都是地位和财产所无法替代的优势。对个人来说,他的人格乃是当他孤独时与他形影相随的东西,乃是任何人也无法夺走或给予别人的东西,人格要比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更本质些,也比所有人对他的评价更实在些。
一个理智的人,即使处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下,也能以他的思想、他的幻想来获取极大的娱乐;即使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惬意的社交,没有剧场,远足和消遣,他也能避免愚人的烦恼。一个生性善良而且性格温和的人,即使贫困也会感到幸福。相反,如若一个人生性贪婪,嫉贤妒能,心狠手辣,即令他是世上最富有的阔佬,也会痛苦不幸。
对于高度理智并对自己独特的人格乐此不倦的人,人类所追求的多数快乐简直是徒劳多余的,它们甚至是使人痛苦烦恼的重负。所以贺拉斯说过这样的话:即使许多人被剥夺了生活中的奢侈品,他们依然能够生活。苏格拉底看到四处都是待售的各种奢侈品,禁不住惊呼曰:我不想要的东西在世界上竟然如此之多。
所以,人生幸福的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除了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作用的因素外,别无其他原因。而且,它与其他两类福事不同,它不是命运的游戏,也不会为我们所曲解;另外两类福事只具有相对价值,而人格则具有绝对价值,因而这就比人们通常以为外在地支配一个人要困难得多。但时间是全能的原动力,它主持公道,在它的影响下,各种生理的和精神的优势会渐渐逝去,而只具备道德的特性是难以达到幸福的。考虑到时间的这种消极作用,另外两种福事似乎要比第一类幸福更为优越,因为时间并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两种幸福。
而且这两类福事也许还有一种优势,即由于它们完全是客观外在的,所以它们能为我们所达到,至少所有的人都有达到它们的可能。相反,主观的东西则不易为我们所获得,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神圣的权力而达到,它是不可变异的、不可让度的、残酷无情的。歌德在诗作中曾描述,人们刚一降世,便被某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着,所以,人只能在为他所设计的范围内求得发展,如同星星之间只能通过相互关联而在轨道中运行一样。所以西比尔和预言家们断言,人绝不可能逃过自己的命运,即使时间的力量也不可能改变人们将耗费一生的人生道路。
我们唯一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并顺从这样的娱乐而且也把它们称之为游戏,力争它们所容许的完美而不顾其余。因此,人应当选择最适合于个人品质发展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试想像一位力大无比的大力士,被环境所迫而从事某种不活动的职业,如从事精巧仔细的手工,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和需要其他能力的脑力劳动,从事正好为他能力所不及的工作,被迫放弃所具有的那些优秀的能力,像这样被命运所安排的人在其一生中绝不会感到幸福。那些被迫使其能力无法得到发展和利用而去追求一种不需要自己能力的职业的人,如果他的理智能力的程度越高,他的命运便愈悲哀,也许让他从事某种体力劳动,他的力量就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们应当注意避免可以预料到的危机,不要以为自己具有某种并没有的能力。
由于隶属第一类的幸福比隶属另外两类的幸福更重要,所以,旨在于保持我们健康、培养我们各种能力的行为,显然要比一心聚敛财富的行为更明智。对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一定就错。严格地说,财富乃是十足的奢侈品,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倒是有许多富豪感到不幸,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精神教养或知识,因而他们无法对他们能够胜任的脑力工作产生兴趣。在真正自然的必需品得到满足的范围之内,一切能够获得的财富,对我们的幸福影响甚微。
的确,倒不如说财富会扰乱我们的幸福,因为聚敛财富不可避免地将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烦恼和不安。然而人们在致富上所费的心思要比提高教养的用心大出何止千百倍,“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对于幸福显然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在看到有人为了聚集金银财宝,就像一只勤劳的蚂蚁,从早到晚无休无止,禅精竭虑,我们就会明白许多道理。他只知要达到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其余便一概不知;他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因此不易受其他事物的影响。
那些最高的快乐,亦即理智的乐趣,乃是他所望尘莫及的;他恣情纵欲,徒劳地以那些瞬息即逝的快感来代替理智的愉悦,并以巨大的代价来延续这种短暂的时刻。如若他运气好,那么他的努力会使他真的积聚起万贯家产,他或者将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嗣,或者继续增加这笔财产,或者挥金如土,浪费这笔财产。这样的一生,尽管他有着真诚执着的追求,也仍然像头戴锥形小帽哗众取宠的小丑一样愚蠢。
“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乃是幸福的契机。一般而论,财富是微不足道的,绝大多数无需为摆脱贫困而奔波的人,与为了财富而耗费精力的人同样感到不幸。他们内心空虚,想像枯竭,精神贫乏,所以这两种人变得相互为伍,他们有着共同的欲求,寻欢作乐,而他们的乐趣大多是感官的快乐和各种消遣,到后来是狂纵无度。纨持子弟过着一种依靠巨笔遗产的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常常在臆想不到的极短时间里将财产挥霍一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空虚无知,所以这种人对生存也感到憎恶厌弃。他来到世上,外表富实而内心贫困,为了用外部的财富弥补内心的不足而作徒劳无益的努力,并竭力去取得虚有的一切,这就像一位寻求某种方法使自己力大无穷的老人一样,大卫王和马雷查尔·德·里克斯就试图这样做。
对于造成人生幸福的其他两类福事的意义我毋需多加强调,现今,人们谁都知道这两种福事的价值。第三类似乎没有第二类重要,因为它不过是别人的意见而已。然而,所有的人仍旧追求名誉,即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只有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满心巴望着高官厚禄,对于名声则少有注意。
总之,一般的人把名誉看作是无价之宝,把名声看作是人能获得的最宝贵的福事,有如上帝选民的金羊毛;只有白痴才会放弃财富而追求地位。而且,第二类和第三类福事互为因果,其他的优势可以常常使我们得到所欲得到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