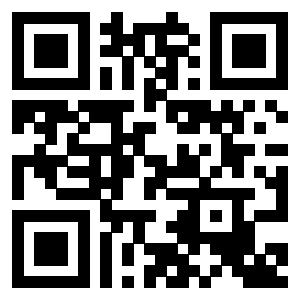衡水中学学神之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拼命努力的自己
本文作者韩思雨,衡水中学2016级毕业生,2016年河北高考文科第7名,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1
涂尔干曾说过:“教育使一个人系统地社会化。”这句话非常正确。
我是在村里上的小学,只有几间教室,操场就是一块尘土漫天的空地。教室里桌椅是残缺不全的,连粉笔也要节省着用。老师资源非常匮乏,大部分是村里上过中专的年轻教师。即便如此,一些教学水平高的老师还是会被上级抽调到县、乡等更高一级的机构教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身边许多人外出打工,孩子也随着他们向城镇流动,农村学校的生源也锐减。从上一年级到上三年级,班里的同学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到四年级,就只剩下四个学生。周围的私立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资源丰富,生活条件好,可是高额的费用把我阻挡在门外,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经济地位导向的今天恐怕无法实现。我不得不和另一个同学的转入了县里的一所公立小学。很多时候我的学费是父母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我也一直接受国家给贫困学生的补助。
父亲一直是我学习道路上的激励者。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第一,没有其他的捷径,教育是通往更好资源和更高平台的阶梯;第二,精神上的怯弱比物质上的匮乏更可怕,人活着不能没有上进心和志气。第三,凡事追求第一,这是成功的最大保证。”我感谢父亲。他没有给家庭带来优越的物质条件,但给了我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世界。
我的性别和社会地位曾是我接受教育的一大障碍。除了父母,身边的人都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学,应该早早相夫教子。母亲上到高中就辍学了,深受其害的母亲坚持让我上学。一位同学的父亲,某局局长,来我家做客时和不屑地告诉我:“以你的家庭条件,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高处不胜寒啊。”
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既然有着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制度,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转学伊始,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然而家庭的责任和父亲的叮嘱让我一刻也无法懈怠——也许这样说非常不学神,但我还是要说,至少在那时候,责任和渴望的激励远大于学习的兴趣或乐趣。有很多学弟学妹问过我,是怎么建立了对学习持久的兴趣,其实我想说,一开始真的是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未来负责,然后慢慢变成了习惯。我们坚持一件事,如果能出于热爱固然好,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恰好热爱、恰好喜欢的东西;如果不能热爱,那就请用责任坚持下去。
我当时总会在做完所有的作业之后才和小伙伴一起玩,每天坚持写日记反思和约束自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不是很明白除数和被除数,有一位姓贾的老师,经验丰富、教学严厉。她把我叫到到讲台上用手挡住一部分数字,问我哪一个是除数,哪一个是被除数。我看着她锐利的眼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诉她答案,竟然都对了。从此我的自信心增长了好多,逐渐赶上同学的步伐,不负父亲的期望一直保持第一。
这所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我这么小离开家自然不适应。但是,在学校期间,母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看望我,我会在别人家长来的时候充满羡慕,自己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每当课前唱歌唱到“烛光里的妈妈”时,我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流。想家是常有的事情,但毫无办法的我开始自我心理调适,逐渐坚强起来。我是半个月回一次家,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都是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看着吃力地蹬着自行车的父亲,看着眼前慢慢掠过的风景,心里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教育改变我现在社会底层的命运。
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在我的县里念的,接触的同学也是一个同质化的相似的社会群体。
首先是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与周潇笔下的农民工子弟“小子”十分相似。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有着社会、制度以及自身的障碍,但是大多数人成绩平平,有低有高,渴望优秀的成绩又不希望付出努力,家庭的教育也没有向他们极力渗透教育的重要性,我的很多同学在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就去打工,最终走向了“阶级再生产”的强大洪流。
另一类是更高层的社会阶层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政府公职人员、教师、上层企业家等。他们有着更好的教育机会,眼界和能力自是不一般。我的一个女同学从小学习奥数,数学成绩在学校可谓傲视群雄。他们在学校一般都很努力学习,这和维持地位、声望和权力的家庭教育分不开。他们的家长很多时候拿我和自己的孩子比较,激励着自己的孩子超过,这和前一种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比。家庭积攒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让他们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我,则是前者社会经济地位和后者文化资本的结合。
我看到周围的亲友都在为生计奔波——是真正的为生计,为糊口,为一个月几百上千块钱辛苦奔忙——后来读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写作文,说看到自己的父母为生计奔波,每月只能赚两万块,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不想“被动地面对教育制度,平静地服从他们被社会化为唯唯诺诺的工人”。初三时,我的总成绩在县里稳居第一,被衡水中学提前录取,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
2
衡水中学是典型的科层制结构。不同年级之间会被分为不同的部门,每个年级有年级主任。老师也会按照学科和班级划分为不同的小组一起进行教学,不同小组之间要进行教学评比。
老师分工明确,按教学成绩来评定等级和职位。学生就是要每天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在管理上相当于在学校等级的最下层。就像《1984》中的“老大哥”对民众的监视一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监控之下。上课的时候会有专门的巡视老师,见到有同学“不专心学习”会记录下来并计入量化。因此这里有着各种“奇葩”的违纪行为,比如有同学上课转头看表被记为“说话未遂”,女生揪头发被弹手……而且违纪是被具体到人的,一般会具体定位,比如“南后二左一”。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极其严苛,后来也习以为常,外在的压力逐渐化为内在的自觉规范。
学习也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刚一进入衡水中学,我并不是太适应“生产链”式的教学方式。老师上课之前会发一张学案让我们提前预习,上课的时候讲学案,在各个学科的自习课上做作业。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从早上五点半起床到晚上十点睡觉,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学案、自助。我出去接趟水的功夫,桌子上就铺满了一层卷子。当时的生活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会有紧张和焦虑的。记得有一次,我写完英语作业把卡涂错了,英语老师非常生气地找到我,让我涂满了整整十张卡。
每一次的作业、周测、月考、期考,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变动的成绩,面临自己身份的重新洗牌。在这里,我们的“先赋角色”毫无用处,每个人关心的只是成绩——我们靠自身努力获得的“社会角色”。高一新入学,来自教育水平不高的小县城的我并没有优势,第一次考试就考了五百多名(当时新生大约三千人)。
之后文理分班,受周围老师和家长们“男生适合学理科,女生适合学文科”的观点影响,同时相对而言我的文科确实好于理科,我进入文科班学习,成绩也逐渐上升并稳定下来。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考试又频繁得像是吃饭,每次考试都是一次“旋转门”,每个人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高峰和低谷,考得好的下一次不一定考好,考得不好的下一次不一定不好,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对成绩耿耿于怀的我们竞争极其激烈,每天十二点三十五还有没有走的人继续学习,吃饭两三分钟绝对解决问题,一下课会有一大群学生主动问老师问题,当然还有午休的时候冒着被记违纪的风险在看书……
每堂班会课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场“精神”的洗礼,班主任会用大量鼓舞人心的事例来教育我们潜心学习。班主任班会上介绍了一位考入北京大学的学姐的励志故事,还让我们把她的回忆录贴在桌子上,每天晚自习的时候全班一起读:“我是五三零班考入北京大学的×××,我真正的拼搏就是在高三。那个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教室里悬挂着“鲲鹏展翅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十二载潜心铸剑,今朝及锋而试”“勤学苦练,万念归一,血拼到底,我必成功”的大幅标语也在无形地暗示我们既然无法改变高考体制,那么就只能借力成功。
同龄人的影响也是我能够成功进入清华大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的身边全部都是为了一个专一的目标甘愿忍受艰辛的人。班级之间有着极为激烈的竞争——学习、卫生、跑操、纪律的评比。班级的荣誉将我们牢牢凝聚在一起,让我们有着极高的群体认同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分享学习经验,交流学习心得。另一方面,我们之间的竞争也丝毫未减。同学之间进行着“赶工运动”,相互比着学。有一次是假期,但是全班同学全部自发在校自习,已经很晚了,班级里的同学没有一个离开的,老师站在门口说到:“现在已经九点五十六了,你们怎么还不走?”这时没有一个人抬头。沉默了一会儿,一位同学站起来,说:“老师,十点才锁门。”在这种学习的氛围中,懈怠的消极思想也会被努力奋斗的正能量所同化。同时,同时学校也会请来大量优秀的毕业生来做演讲,和我们交流学习的方法和成功的经验。这种社会和文化的资源让我们受益匪浅。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衡中几乎是一个杜绝了鸡血和逆袭的学校——将学习通过极佳的教学水平和标准而严苛的流程规定下来,只要拼命努力跟着做,一步一步内化提高,成绩终究不会差。而我的学习经历,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很多学弟学妹在找我咨询高中生活的时候,都明显地表现出对“逆袭”的渴望,我感到不能理解。逆袭本身就意味着之前一个不用功的过程,能逆袭成功固然好,可是为什么非要这样浪费时间?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如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忧虑,如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如果说在人生的前19年里,我骄傲过什么,那就是我从未怯懦,从未退缩,从未浪费时间,从未被任何困难打倒。
我的确有着比别人更低微的社会地位和更匮乏的社会资源,然而依然可以在这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利用教育制度,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社会底层,努力奋斗到与别人平起平坐。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归根到底,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拼命努力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