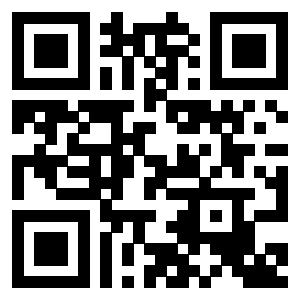年轻人为什么不该呆在小地方?
年轻人为什么不该呆在小地方?
文/周冲
昨天洗脸的时候,美容院的小姑娘说,听说北京很大的雾霾,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太可怕了。
另一个说,是啊,空气越来越糟糕了。
先前的接着话茬,聊起了老家与都市的区别。
在老家,天蓝如绸,夜晚的时候,星星又大又低,河水清冽,鱼虾跃动,堤岸上柳枝撩人,漂亮得连最好的公园,都像是一个赝品。
我问她,那你想回去吗?
她说,老家虽然自然环境好,但太封闭了,人的格局也太小了,还是应该活在开放点的地方。
众附议。
皆言:然。
一个说,说句不好听的,在小地方,你换了两个男朋友,都会被当成一个荡妇。
我也是从小县城出来的人。
一只赣地土妞,一身泥巴味,半生小地方生活经历,因此,对她们所说的,并不陌生。
固然,小地方消费水平低,环境好,空气无污染,瓜果蔬菜亲手种,无农药,没化肥(这还是农村才成,县镇以上,都得买),吃得延年益寿,万岁万岁万万岁。
还有,不堵车,从东头到西头,只要打个屁的时间。
而邻里乡亲领导同事,都是熟稔的亲朋,好办事,好说话,四通八达,任何破事都能找得到后门。
舒服吗?
当然。
简直是过上等生活,享下等情欲,付末等劳力。
然而,以上种种给我们架构的,却不是一种自由、公正、有趣、充满未知的人生,
每个人年少轻狂时,都曾隐隐告诫过自己:当我长大,万不可成为那种人——那种人,正是小地方正批量生产的人。
小地方固有其善,亦有其美。但,之于一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弊病:
因为封闭,守旧,求稳,小地方变成一个庞大的玻璃罩。在这个罩子里,一切以和为贵,以集体为重,以表面的风光为荣。
个体的个性化,自由意识,对权威的质疑,对固有观念的挑战等能力,都会被压抑,然后慢慢被环境所消解。
而思想的不开放,必然也导致身心的不自由,对他者与自己的不宽容,道德绑架,窥视成风,一如楚门的世界。
每个人,都是没有作品的演员。
2,资源匮乏。
人文的。物质的。社交的。
当年在小县城,犹记得对周围人说,想看一场话剧。被骂装逼。因为没有,便认为不存在。
就像一口千年火锅,原本都是下锅菜,煮着煮着,都成汤料了。
倘若你是一个异类,那么,必成《刺客聂隐娘》中的青鸾:
一个人,没有同类。
不论是非,只论亲疏。
不看高下,只看背景。
原本勇于担当的,都在各种后门里来回。
4,反智。
反文艺。
反思想。
反知识。
遇到争执,对言说者态度的在乎,远大于对是非、对错和真相的在乎。
犬儒主义者遍地,不仅自己不相信奋斗,反而以过来人的姿态,嘲笑奋斗。
最后,形成一种怪异的审美:以粗鄙为美德,以堕落为常理,以邪恶为个性。
5,生活没有质感。
敷衍过了工作日,周末或夜晚,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只有麻将、淘宝奔跑吧兄弟。
要么八卦成性,蜚短流长,舌头在各种人的下半身来来去去。
6,缺乏界限。
随意打探隐私。
你为什么不结婚?你多少钱一个月?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你买房了吗?买车了吗?有对象了吗……
公域私域不分。
讨论公共事件或现象时,不出两句,马上改为攻击隐私。
平庸之恶无处不在。
7,拜权拜钱。
关注点永远是:谁的官职更高,谁的车更贵,谁的房子更大,谁家女孩更鲜嫩多汁。
……
以上种种,我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活蹦乱跳的例子作佐证。但我想,这是任何在小地方呆过的人,都感觉得到的共识。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路西法效应证明,人在不同的制度中,不同的社会情境里,其意识和行为,都会呈现不同的变化。
宽容自由,充满尊重的环境里,我们可能都是身揣小马达,心怀小太阳的有志青年;
然而在另一种守旧的环境里,我们可能就变得暮气沉沉,未老先衰,成为父辈的翻版。
《变形记》里,有一期是林依轮的儿子变形。
他是优雅如王子的男孩,贵族范,文艺气,言谈举止,都可看出良好的教养。
然而,即使是他,在陕西农村里,面对粗蛮无礼的同伴,无法自控地动怒流泪,后来言辞无礼,几乎要打起来。
进入一个环境,一个群体,就进入一种特定的秩序。
你必须顺应这个秩序。
而制度一旦被认同,人的行为必被塑型,亦会影响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
环境改变,规则随之改变,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重构。
这就是津巴多所说的“情境的力量。”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人性的脆弱彰显无疑,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反观现实,我们也经常看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式的场景。尤其是当人们丧失了自我意识,就很容易被他人、形势、环境等大趋势所驱动。
莫罗说:“我们都是自身情境的囚徒。”
去一个广袤的世界里,那里或许压力覆顶,冷漠遍地,势利横行,但自由同样无处不在。
你犯了错,都有机会重头再来。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说,小地方也能出人才呀,比如湖南湘潭的某农民儿子。
其实,这陷入了基本归因错误。
人们在考察原因时,具有高估倾向性因素(谴责或赞誉人)、低估情境性因素(谴责或赞誉环境)的双重倾向。
我们单考虑他的出身,却没有想到,他的教育地、起势地、指挥地、以及后来的权力中心,都在都市。
小地方还是大城市?
这是个被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
然而,我还是觉得,抛去物的因素不讲,在都市生活,我们会更忠于自己。
我们家可二因为重度躁郁症,从《新快报》辞职回万载时,我非常担心,他虽然聪明得欠打,犀利得招人烦,但越是如此,书读得越多,心中越有谱,在小地方就越格格不入。
我说,回去干嘛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不,虽然药没停,状态却越来越差,终于又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