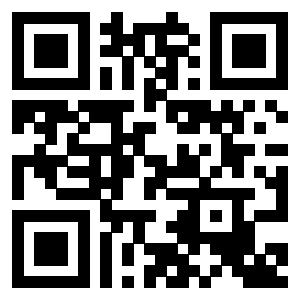一位70后的感慨:下半辈子我会陷入贫困吗?
文/刘黎平
我一直是个有着忧患感,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人。
从一个小悲剧说起吧。
十多年以前,听家乡人说,父母生活劳动过的生产队,有一位长我十岁左右的大哥,在铁路旁电线杆上贴假证广告,被警察追赶,中枪,还算幸运,打在腿上,之后扭送回乡。
吃了子弹,在我们当地是一件很不幸、很耻辱的事,怨妇骂丈夫时,最严重的一句话就是:“红炮子穿心的”。这位老乡的遭遇在当地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老乡姓毛,外号光头哥,曾何几时,他们毛家曾是方圆十来里的“显族”。
光头哥父亲名字中带一个“敏”字,职业是漆匠,人称“敏漆匠”,手艺祖传,传到他手里,不知是第几代。
从他所在的生产队往外走十公里,没有第二个从事漆匠手艺的。他所从事的产业,其附加值,远远高于社员们在地里刨一锄,挖一铲的劳动,他很为此骄傲,用了一番很形象的话来概括自己的成就感:“我虽然是农民,可一辈子没下田沾过泥巴沾过水。”
那个时代我所生活的农村,虽然极其贫困,社员们经常用地瓜当口粮,然后,敏漆匠家中顿顿有白米饭,天天能喝酒,坛子罐子里的腐乳、辣椒酱,墙上的腊肉干,没断过。
异于常人的富贵,全源于他手中的活儿:刷漆。
敏漆匠很豪爽,很大度,我们家在1979年回城后,将乡下的房子作价一百来元卖给他家。后来,我家请木匠做了一个衣柜,请了一个蹩脚漆匠,刷得实在对不起行业平均水平。
敏漆匠听说后,立即叫他两个儿子进城,吩咐说:“你们帮老乡刷好柜子,一分钱都不能收,包括油漆成本。”
这种大度和豪爽,半源于性格,半源于行业的骄傲。因为,我大度得起,豪爽得起。
再过十年,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城的乡亲和父母聊起敏漆匠,皆叹息:漆匠家中光景,泯然众人矣。
又数年,则说:漆匠家中光景,不如众人矣,儿子孙辈得出去打工了。
父母听了有些惆怅,很为这位生产队显族的没落伤感,我当时是一位师专生,在旁边听着,全是一种局外人的感受:时代在前进,你不前进,多少有点活该。
父母在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眉毛都能长三寸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荣耀有多大,用头发都可以想象出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样霸气的分贝,那样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这也算是一种传播的优势吧。
记得当时我去上学,从播放着“中国心”、“回娘家”的营业大厅里走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销售企业的那种荣誉感,也延续到我这个小学生身上,让我有如同从中南海走出来的豪迈感。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公司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无比张扬的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持续下去,他们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明天,反正处在同一个领域:幸福。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我们70后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难怪当时一部名为《子夜》的电影,是根据矛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让影评家吐槽:电影的主人公哪里像民国上海滩的资本家,完全是党委书记在做报告吗。为什么?是当时的经济形态决定了艺术形态。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性特征,站在高处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这和家乡漆匠为什么豪爽、大度,都有同一个缘由:行业的独一性,不可替代。
姑且举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懒得动身。某日,有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售货员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傲慢,来自于行业的独一性。
然而,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但是当时全班一百多号人(有大量复读生),只考上九个。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张大姐,你的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公司子弟能读书的不多,骄傲,蛮横,不学技术,现在尝苦头了,你们家小刘不错,争气,不会进入下岗大潮。”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波比一波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员工们还在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身份来安慰自己。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实地降临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大家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那一次,没有几个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种与以前的体面相称的工作方式。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且隐其名,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我的同辈中也有,有一位小学同学,顶职在一家国有销售公司工作,后来娶妻,家居电器都买好了,结果碰上公司倒闭,新娘不干了,不来了。
下岗女员工,是那时人民教师配偶的一个重要来源。教师钱不多,但稳定,女公务员不稀罕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互相将就吧。
娶妻和我学历不对称,这也让我很忧患。
那时的我,好像“平凡的世界”里的朱少平,不安于平淡的乡村教师生涯,要走一条异样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鲁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我终于走了一条和前辈们异样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如今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夜,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我如同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热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满天神佛,列祖列宗,听见我真诚的呼唤,我进入一家大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是一种耻辱,人的落寞,往往是因为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我这个70后的小知识分子,和他们那帮倒霉蛋是不同的,我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说这话,似乎有点自命不凡,但是,进入新闻行业的人,有几个是自命平凡的呢?
说实在话,除了父母亲人师长,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从事的这家纸媒,广州的一家巨型纸媒。一些离开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过它,但是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不是谨慎,而是真诚。
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理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外传播,让我走在路上能遇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全国报业第一不说,居然还胜过正在兴起的芒果台。纸媒的广告收入超过几乎同级别的电视台,这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我那时也不能说没有危机感,忧患感,因为我们经常要从网上找最新信息来源,记者们要等网上的央行加息减息消息,看新闻,往往第一时间上网,然后才考虑报纸。
然而,我的忧患感,仅仅停留在纸媒与网络平等竞争的层面上,报纸在新闻传播领域,虽然将来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但至少是一个较大较强的存在。
而且,劳动人民对于报纸质朴的情感,似乎也对我有着心理抚慰的作用。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知道我是报社的,很羡慕地说:“报纸好啊,国民党要办,共产党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这句话胜过千万句经过精心策划,引用了海量数据的精英人士的报告,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其实,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换,就是“报纸”要替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没想到这个行业,广告在呈现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很多家纸媒已经在传播这种声音。
随着这种声音到来的,是很多纸媒精英肉身的死亡,不明白为何行业的式微,要以人的生命作为祭奠和注解,莫非这就是共业?就是劫数?
有一回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还能在账面上没有下滑迹象,年终奖季度奖照发,尽管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星期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实在是很没面子。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前面的林荫大道上,看着他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楼。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神,充满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憧憬,我忽然有点紧张,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贫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走运,不够努力,可能还得将这种贫寒延续下去。
有一部美国短片小说,讲一个小孩听说班里要捐助贫困家庭,善良的他也拿了东西捐出来,结果老师很无情地告诉他:“某某同学,你不用捐献,因为学校捐助的,就是你家。”当时那位孩子愕然之后的泪花,会是怎样一种心痛呢?
我惊恐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刷得荡然无存。
我想起家乡曾经富贵的漆匠,他的儿子在铁路旁贴广告挨枪子,想起母亲公司那位曾嚣张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炒米饭,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我当时引以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临的。
引用我曾经写过的一部玄幻小说:《一位史前暴君的笔记》,里面有这么一番话:“年幼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拯救这个星球;年少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拯救这个帝国;年青的时候,我以为我能拯救这座城市;中年的时候,我发现我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悲哉斯言。
幼稚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好像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出现像产业工人那样的退出潮流。如今的这一群,是高知识高素养的一群。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品质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潮流,一种无法用失误和卑鄙去谴责的潮流。
它总会来,它总会发生,它总会选择某一人群,如果你不幸被选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选中,你能做到的,似乎只有跟着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说“人穷志不穷”,物质上穷了,精神也会跟着沦丧。即使在提倡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一个生产队里,最穷的那一户也是受嘲笑最多的一户,更何况今日。
我们很可能成为被照顾的一群,拿着国家的救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高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愿意去领救济金。
士可杀不可辱,在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不舍曾经有过的一份光荣感。
漆匠、营业部主任,失去的也是一份光荣感。
纸媒的人,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可谓五花八门,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推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要不懒,不太蠢,饿不死人。
早知道如此,不如早一点去炒粉,去卖菜,去开班,在这些行业早一点折腾经营,凭着当年考入名校的智商和毅力,或许早就开上连锁店,当上土豪了。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理财。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然而,凭借你在新闻界积下的那点子银两,在失去营生行业的情况下,它们的利息完全不够你保证下半辈子的开销。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下跌的股票,没有永远高利息的理财产品,更何况你的基数也就那么一点点,要跟上通胀的速度,它们得翻倍地增长,有这样的事吗?扪心自问一下吧。
新闻在碎片化,在个体化,新闻传播主体也在碎片化,个体化,新闻从业者想要保持那份荣誉感,使命感,在保持主业的同时,微信是维持这种感觉的最合适平台。
问题是,这种职业感觉可能会延续下去,但往昔的那一点点收入上的优越感(其实也很不实在)却再也维持不下去。
阅读量就算屡屡达到100000+,粉丝一万、两万地涨到十万,可是大部分人除了在朋友圈,在手指的划拨中获得一种数字刷新上的快感之外,真金白银,一分也没有。
尤其是本人这种,纯粹是赚吆喝的。觉得和当年在中学办文学社,分发那些布满浓稠油墨的文学小册子没啥子区别。
对整个行业,我一直是个路盲,但我对那些口水救世主也没有什么信心。
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先知先觉者,一种新的行业形态,谁都预言不了,就好像从来没有经济学家能预言到经济危机一样。
听过很多的关于新媒体的报告,讲座,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算是占了威权力高度的澎湃,听说点击量也在断崖式的下崩。
新的新闻形态,它一定有,一定有它的理存在着,就好像朱熹说的:凡是事物,事先一定有一个理存在。
然而,世界是神秘的,不可知的,谁都摸不到这种新媒体形态的理,谁都不能准确描述它的具象,谁都说不清楚它何时来临。
就好像罗斯福新政,谁都以为是他挽救了美国的危机,谁都没有想到是一场超规模的战争挽救了美国的经济。(注:罗斯福、二战并没有挽救美国)
是二战挽救了美国,挽救了西方,然而,在这场挽救的过程中,是亿万百姓的痛苦和士兵的牺牲。
我们新闻人摸索着走向那个新的媒体形式,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摸索过程和未来的情状,但可以明白的是,我们也要经历新闻的“二战”,会有很多牺牲,很多痛苦,很多彷徨,或许不幸,只是不知道谁会面临这些人力与时代力的摩擦。
作为自封的太史,我只能暖男式地说一句:摸索前进的路上,我们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