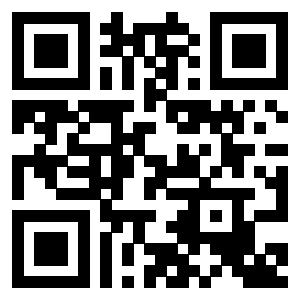少年远方
文/洛洛
那是个初冬,雪被风荡着,一点没一点地下。到了傍晚,雪下大了,衬着冬日的晚霞,天空如一匹被白雪珍珠缀上的红色缎子,被风刮出了优美的层层波浪。波浪流入人间,撒一地醉红色夕阳。这夕阳里一位男人身影走动着。
这个身材矮小清瘦,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人是我父亲。他长得不好看,一头乱兮兮的黑发,后背略佝,鼻翼塌陷,还有双目空一切的眼。后来我知道,父亲的眼里并不是完全目空一切的,那是他眼光的聚焦只在一个人身上,只有一个明确的点,所以周围的一切自然给失焦了。父亲眼中的那个点,是个直发及腰、着一袭月白长裙、眼神却世故、老成的少女。这个女人后来成了我母亲。
大致是这样,一个初冬的傍晚,雪下大了,他又悄悄跟上她,跟上她前去约会的脚步。此前他已跟了她几个月之久,对她每天规律性的生活了若指掌。每天下午6点,她会准时在电影院门口等她当电影放映员的男朋友回家。
可今日却不同以往,她等到男朋友之后,脸上不再有微笑了。他远远看着他们手舞足蹈,吵架的声音被大风吸进雪里。然后他看到她的男朋友抬手扇了她一巴掌。
他知道原因。这个小城对她的流言蜚语从不停歇,八十年代末的社会还不开放,她的一切行为在人们眼里都是怪的,并且可以被称为“风流”。在她的风流背后,蠢蠢欲动着一帮男人,都想沾惹些她的风流。我父亲就在其中。
此刻,父亲却不想再做她背后的追随者了。他短粗的腿几个跨步奔到她和男朋友面前,抬手就给了那男人一拳。两个男人滚在雪里,打得鼻青眼肿。他们身边的少女哭得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她的哭是因为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还是突然杀出的小英雄把她感动了。反正她一直哭着,最后她和他一起走在回家路上了,她还是哭着。
他那时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脸颊上已经爬出第一层络腮胡。他长得丑,却因为是市里唯一的大学生,所以也有不少女孩喜欢,但他谁也不接受,人人说他前途一片光明,以后肯定是不会留在这个落后小城的。但只有他心里明白,他目空一切的眼里早有了她。
母亲每天的约会改了对象,变成了在雪地里默默追在她身后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每天都在电影院到钢铁厂家属区的路上散步,像几个月前她和放映员每天走过一样。但是他们不说话,有的只是她时不时的一声叹息,还有从这叹息声中猛然抬起头望着她的他。
一个多月的寒假过去了,他出发回大学前,她把他叫到家里。父亲由此得以看到她全部的生活:一个小铁锅,一把折叠的简易小木桌,没有凳子,只能坐在简易铁床上。父亲想,在这铁床上曾“咯吱咯吱”生出过多少情事?现在他的情事也要在这铁床上发生了吗。
果然就发生了,她当着他的面把衣服脱掉,然后换上一身很薄的轻纱睡衣。她的衣服真是多,各式各样的,都是她自己设计,又跑到省城买布找裁缝做的。她走近他,身体贴近他,然后她把他紧张到颤抖的头发上的一根鸡毛拂掉。他在来她家之前,刚刚放过鸡。
她哈哈大笑,这笑放浪了,成了流言蜚语里的那个她。她说:“我在你眼里是这么个人吧?”他倔强地摇摇头。她又换了样子,脸转过去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雪景,说:“你是唯一真心待我的人。”
最后,他把自己的日记本留给她。那里面装着他对她全部的思念,从几个月之前第一次在全市文艺汇演上见到她,一直到昨天,他一直没断过对她的思念。他从没想过自己能离她如此之近。他写道:“我不知道你以前受过什么伤,但我想保护你,等我大学毕业回家乡,我娶你!”
母亲在他走后,每天都会抽时间读他的日记,直到那本日记上的纸页被她的泪打得湿黄。两年,他没有再回来,信也是寥寥几封。当她有点怀疑曾经他的真心时,他回来了。
人人都说父亲傻,为了个不值得的女人放弃大城市的分配工作,回到穷乡僻壤。他回来的第一刻就去她家里找她。穿过幽深肮脏的走廊,他立定在门口,整整衣服,轻轻推开没有关严的门。她似乎正专心写着什么,竟没有被声音惊动。他俯头一看,发现信纸上飘满她的泪。他只看清了一句“我不能耽误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突然抱住她。母亲把身子终于给了他。
母亲有了我之后,才彻底被爷爷奶奶接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发现父亲对母亲的爱就像个小男孩,胆小甚微,带着极强的宠溺之心。母亲从不抱我,都是父亲把我喜笑颜开地拿到母亲面前。于是,小小的我的眼里就有了母亲勉强挤出的微笑,或一句“别烦了,我在设计”。父亲也没觉得自讨没趣,还是每天不厌其烦地,要把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近一点,更拉近一点。我再大一点时,知道了母亲的不快乐,看到了放在抽屉深处的抗抑郁药,也曾在深夜里看到父亲偷吃母亲的药。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要吃药的原因:母亲每天都会把“百忧解”一颗颗倒出来数,这样她才记得今天到底吃没吃过。为了能让她少吃几天“百忧解”,父亲只好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替母亲解忧。
母亲的服装品牌终于走出县城,上到全国舞台时,我八岁。那时父亲被药折磨得秃顶了,成了更丑的男人。母亲也被药折磨得满脸皱纹,眼睛成了父亲少年时的目空一切。母亲要去北京参加服装设计节,坚持不肯让父亲同去。他给她收拾箱子,八月带了满满的冬装,说北京冷,穿不了短袖裙子。母亲笑话他,却接受了。母亲临行前一阵,我又偷偷看到父亲半夜起床,给母亲腌制她喜欢的萝卜干。我想吃几块,父亲头一回说不。他说:“你妈去北京两个月,饮食不习惯的,没有这个她不吃饭!”
送走母亲后,父亲走在长长的大马路上,边走边哭,像个小孩遗失了最心爱的玩具,那种哭是埋在平静下面的歇斯底里。我像个大人拍拍他的肩,问他:“你知道妈妈活得不开心吗?”
他诧异地转过头,木讷地瞧着我,似乎想不到才八岁的我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或说——戳破了这个真相。
也许是我意料之中的,但绝对不是父亲意料中的:母亲隔了一整个冬天都没回家。服装节早过了,母亲也从没联系父亲。这次,他真正把母亲留下的“百忧解”当药吃了,甚至比母亲之前吃的剂量还大。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收拾箱子,我问他:“你干什么?”他说:“上北京找你妈妈!”然后他把一整罐腌菜晃到我面前:“我知道她不肯好好吃饭的!”
我没忍心拆穿他,这个小城里谁都知道母亲和一个服装商好上了。那人是母亲的初恋。
三月初,北京的柳絮漫天飞舞,像春天的雪。父亲拖着我和他为母亲准备的一大罐腌菜到北京二环内的一个高级小区门口。他向保安打听母亲。保安给楼上打了电话。十几分钟后,我看到了消失近一年的母亲。
我和父亲都落泪了,我们像两颗被遗弃的石子,被人扔在路边,被母亲拾起,以为从此有了家,却忘记了我们只是石头,结果又被扔回路边。
她烫了卷发,脸上的皱纹被白粉遮没,整个人看上去比以前在家时健康年轻。她没事人一样,脱口就问:“带离婚协议来啦?”她一口的别扭普通话让我浑身难受。
我这才知道她是有联系过父亲的。她曾把一纸离婚协议寄给父亲,别的话、别的解释却一句也没留下。
父亲点点头,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和腌菜交给她。她莞尔一笑,说:“现在谁还吃这个!”她顺手把腌菜交给旁边保安亭的保安,把父亲每天放下工作不做,剪萝卜条把手剪烂,又每天不睡觉半夜起床查看腌制程度的,父亲腌得最好的一罐腌菜顺手给了保安。
父亲也笑着对保安说:“好吃呢!”我气得浑身发抖,把腌菜抢回来,拉着父亲就走,把父亲满脑子的话搁浅在和母亲遥远的距离之外。
第二天我们又去找她,才从保安口中知道她和新婚丈夫去美国度蜜月了。回旅馆后,我对父亲说:“看完长城就回家吧。”父亲却一定要把行程走完。他是个有计划的人,绝对受不了计划有变。他的计划是,给母亲十五天时间,也给自己追回母亲的十五天时间。我问他为什么不肯走。他说:“我和你张叔李叔打赌你妈妈能回家,我不能就这么输着回去……”
我知道,他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象。他活在幻象里,觉得母亲还是他的,不管现在她的肉体睡在哪个男人身边,不管她的心现在给了谁。在他的幻象里,母亲被重新捏塑,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一个从十五年前就只爱他的母亲出现了。
他如愿在北京待了半个月,期间我们去了长城、故宫,在旅馆门前的烤串摊上吃了几百串羊肉。我坚持陪他过完了幻象中的与母亲团聚的十五天。
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火车行驶在空荡荡的北方平原时,已是深夜。我从昏倦的睡眠里挣醒,看到父亲把头倚在玻璃窗上睡着了,怀里抱着那罐精心腌制的腌菜。( )我小心地把它抽出父亲的怀抱,扭开盖子偷尝一口。味道不酸,也不太辣,记忆里每次得伴着它才能咽下饭的腌菜,成了平平淡淡的味道。像父亲平淡而庸俗的一生的味道。
母亲再婚后,父亲从此拒绝做腌菜。他总和我说:“给你妈妈打个电话嘛!”我拿起电话后,他又在我和母亲说话的间隙里插几句:“你问她生活习惯吗?”“你问她缺不缺钱?”“你给她说药要少吃!”我把电话塞给他,让他和母亲直接对话。他傻笑一下,接过电话,假装豁达地说:“喂!还好吧?……想你呢!我和儿子都想你!……哈哈哈……”可每回挂断电话,我总看到他要去洗把脸,用冷水把红彤彤的眼睛洗成没哭过的样子。我嘲笑他:“哭啦?”他笑嘻嘻地回一句:“你才哭了呢!不哭,不哭!”
到我十二岁要去北京上学之前,父亲给我做了罐腌菜,让我给母亲捎去。四年后再见到她,她已是服装业里的风云人物,在全聚德的高级包厢里接待外宾。我怯生生地进门,被她一把拉过去,然后用流畅的英文被她介绍着。
我没来由地一阵气愤,把一罐腌菜声响很猛地拍在转动圆盘的精美佳肴中。它显得如此丑陋,又格格不入。母亲的脸霎时垮下来,随即又恢复成满脸堆笑。在笑的间隙里,她把头转过来,温柔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那罐腌菜。我突然间理解了她之前的不快乐。她叹息一声,然后低声和我说了句“对不起,儿子”。我知道这声抱歉也是她对父亲说的。
这声抱歉瞬间被席间的喧嚣杀死了,无声无息了。这声抱歉藏在父亲和母亲的悠悠岁月里,藏在寻常人家餐桌缺席的那个空位之上。
摘自《我只是不想大多数一样》